| 央视网|视频|网站地图 |
| 客服设为首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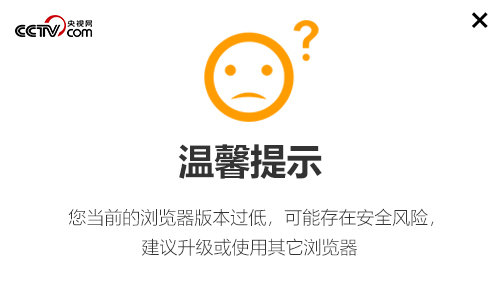
【那段“屯巴拉社与马赫坡社”的恩怨】
在内地版中,这是被删减最多的一条线。所以观众有些不能理解这两个族群的新仇旧恨,也看不出部族服饰的差异,以及为什么有族人宁愿跟日本人站在一边。
在魏德圣看来,“雾社事件”至少滋生了两组仇恨:原住民群体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同族之间的仇恨,即抗日的马赫坡社与日本人的“帮凶”屯巴拉社之间的仇恨。有人会问,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为什么要帮日本人?魏德圣尝试让观众分别站在两个族群的角度看他们各自的立场:当A被C控制,C让A帮忙杀B,如果杀了B,C给A钱,若不帮忙,那C就杀A全家。A应该怎么选择?
旧恨与利诱下的杀戮
场景1:“姊妹原事件”。雾社群被日军封锁多年,在急需补充物资的情况下,日本人趁机唆使布农族干卓万社假借物资交换之名,诱骗雾社群至两族交界之地进行交易。布农族人将他们灌醉之后,趁夜“出草”。雾社群赴约交易的百余名壮丁中,仅有五六人死里逃生返回部落。这一部分,内地版全删。
场景2:土布亚湾之役。“雾社事件”爆发后,在日本人“以番制番”的利诱下,都达群的族人开始协助日方进入山林搜索和猎杀赛德克族的起义战士。1930年11月,都达群总头目铁木·瓦力斯率领56名族人,发现并尾随赛德克族12名战士,准备予以猎杀,于是双方在雾社东北方的土布亚湾溪谷发生战斗,铁木·瓦力斯阵亡。这场跨度极长的“兄弟对战”,在内地版中只剩下几个镜头以及瓦力斯阵亡的结局。
【那段“原住民与日本人”的对抗】
在片中,日军不是以往中国战争片里那种凶神恶煞的魔鬼,日本军官小岛甚至是文明礼貌、英俊潇洒、态度温和的知识分子形象。小岛的参战,缘起于家人在“雾社事件”中惨遭赛德克人的屠杀。雾社一战,一千多名部族壮丁奋勇作战,用土枪大刀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和毒气弹,最后六百多人战死,两百多人自杀。时隔80多年,重提这段历史,魏德圣希望让观众从更大的视角看待这样一个命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反抗就会遭遇灭族、当屈服就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该怎么办?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细节1:赛德克人的酒,是将小米放入口中咀嚼再吐出,以口水发酵成米酒。1930年,在一场马赫坡赛德克人的婚礼上,一位骄傲的日本警察拒绝喝这种“不卫生”的酒,被族人视为无礼,最后爆发冲突,日警被年轻的赛德克人打伤,矛盾升级,最终引发“雾社事件”。片中,日警喊了一声:“不要,我不要喝口水做的酒!”并推倒了达多·莫那,达多怒而击之,族人一拥而上助威。
细节2:在“文明”的日本人眼里,赛德克人的习俗是“野蛮”的。日本政府禁止他们继续猎人头和文面,并教育赛德克族人学习新的耕种技术。片中,日本人收缴了赛德克人辛辛苦苦攒下的人头骨,当莫那·鲁道被收走一麻袋人头骨时,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
细节3:日本人的“鞠躬”和“问好”,是表达礼貌的手段。而在桀骜不驯的赛德克族,这种礼仪是“百教不会”的,这一度让初次驾到的日本官员大为火光。片中,几个日本警察屁颠屁颠迎接新领导上任,在桥上各种点头哈腰之际,一赛德克男子大摇大摆擦肩而过。领导面露不悦,下属连连解释:“他们野蛮人就这样。”
【那份“进神社还是进猎场”的纠结】
魏德圣用了12年时间,花费了7亿元台币,只为问一句:“我是谁?”他一直很想知道,自己的祖辈来自哪里,都做过些什么。如果电影里没有“花冈一郎”、“花冈二郎”这些角色的存在,《赛德克·巴莱》将失去真正的灵魂,同时缺乏讨论的意义。相比起上述两种矛盾,一郎、二郎则真正揪出了人物“个体内心”的矛盾,也揪出了魏德圣逢电影必讨论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是真实人物,这些事也是真实的事件。”他告诉记者:“在做这部片之前,我必须替历史人物想想他们的立场是什么,用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让观众理解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选择。”
一郎、二郎本来也是赛德克人,在日军“以夷治夷”的政策下,他们从小学习日本文化,长大后成为日本驻守当地的警察,也有了日本名字。两个名字,两种身份,他们在对立的双方中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当赛德克人起义,他们被迫卷入一个终极问题:你死后,是要进日本人的神社,还是要去祖灵的猎场?他们无法选择,最终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方式———切腹———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但他使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