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网|视频|网站地图 |
| 客服设为首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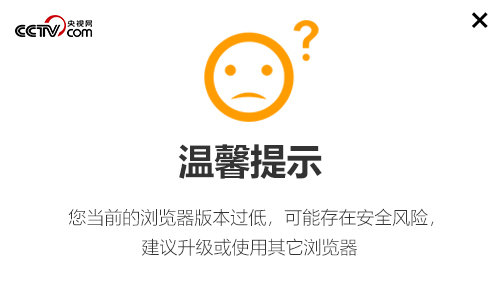
身份与认同的煎熬
对白1:“……夹在族人的期望和日本人的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对白2:“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再过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对白3:一郎问:“头目,被文明统治不好吗?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学校,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莫那答:“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喝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人看见自己有多贫穷!”
【导演阐述】
“和谐,是整部电影追求的关键词”
魏德圣试图用一部电影告诉观众:“学会跟自己的历史和解。”但故事讲完了,他也明白自己会受到多少质疑。在影片中,他不惜巨细靡遗地呈现原住民屠杀日本人的血腥,老弱妇孺、好人坏人,一概杀绝,就连赛德克的孩子也拿上武器,杀掉平常处罚他们的日籍老师、手无寸铁的妇女幼童……“雾社事件真的很难把握。怎么传达给观众?怎样让观众不反感?”这是魏德圣反复问自己的问题。庆幸的是,他做到了。即使全片血腥,但观众却并不感到恶心,更谈不上对赛德克族厌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秘诀1]唯美画面
鲜血、残肢、断头,伴随的却是美得让人无法呼吸的画面———有山川河流,有樱花漫天,有孩子们的微笑,有女人们的眺望。即便杀戮本身,也是委婉的表达方式———第一场突袭战,躺下的日本兵看到了盛开的樱花,如血一般殷红;雾社事件后日军围剿赛德克族,一名被杀的狙击手缓缓闭上眼睛,熊熊火光在他眼里幻化成了樱花;年轻的莫那头目,在山间飞奔追上一名日本兵,回身一刀,只见一缕轻烟,被划成了两半……
“用什么方式展现这个事件,又能让现代人接受?我每拍一个镜头,每拍一个场景,都在想,这样观众能接受吗?”在不断的追问中,魏德圣如履薄冰:“你既然选择拍那段历史,有些东西就不能回避,比如杀人的镜头。你一回避,人家都说你回避历史、改变历史。怎么办?只能委婉一点,比如有女人、孩子被杀,我就不能让电影呈现那个过程,不能让你们看见血腥场面。我只能让那个过程变成一场‘农务’,变成大猎场上猎人在追杀猎物。那是一场原始的打猎,是一种距离感。”
[秘诀2]抒情曲调
在日军进攻村落的时候,在赛德克男人砍下敌人头颅的时候,在母亲与妻子上吊自杀的时候,在年少的孩子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时候……那凄美的山歌总是如期响起,让人心醉,让人心碎。在这种如泣如诉的调子中,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忧伤和魅惑。
“剪完片之后,还是觉得少了什么。尽管我已经尽量替观众想了,但还是不够。后来明白,哦,少一首歌,一首让观众安定下来的歌。”魏德圣选择了沿用赛德克族的古调,沧桑而不失真诚。
[秘诀3]壮美诗词
有人说,导演魏德圣是个诗人,他在片中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诗意发挥到淋漓尽致。魏德圣明白,光有曲调,无法表达“如泣如诉”的效果,于是他先是找到好莱坞填词人,接着又找到一名曾在《海角七号》有过联系的朋友。“我需要一些词,来安抚观众。歌里完全没有批判,只是客观呈现、阐述我们的族群是怎样的。”这是魏德圣提出的要求。在经历了数月创作后,朋友给出了样品,魏德圣摇头:“这些词,要有悲壮有凄美,悲+壮有了,凄+美也有了,悲+美有了,但是壮+美呢?我还需要一些东西,一些能体现赛德克人豪迈地去应对死亡的东西!”
交出成品时,已经到了录制前的最后一天。管弦乐拉响的那一刻,魏德圣只说了一句:“对了,这下对了!”在这些词里,他通过祭司的祭语解释了这个民族的血性:“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