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地图 |
| 客服设为首页 |
By 云也退
“第一修正案不保护帐篷,它保护的是言论和集会。”
10月,纽约市市长布卢姆伯格就“占领华尔街”运动说了这么一句话。在奥巴马带头表示同情以来,布卢姆伯格也加入了默认抗议者有理的美国高官富绅的一员。他也像总统一样,谈到了“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掀掉抗议者们的帐篷”,虽然理由比较冷血:这将动用过多的警力。
将来,当人们给“占领华尔街”盖棺定论时,会不会认为它取得过“阶段性胜利”呢?
对祖科提公园的抗议者来说的确如此:首先,不必管敌人的心虚退让,网民、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口号和行动,无疑在拥有巨额财富与制造罪恶的体制之间画上了坚硬的等号;其次,尽管第一修正案的确不保护帐篷,但是帐篷就是公共空间的言论表达,传递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这个信息,比之前在罗马、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等地用砖头、啤酒瓶、汽油、棍棒表达的情绪要理性而有力得多;最后,11月16日的形势拐点让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得以明朗:在以纽约为首的各个卷入这场大串联的美国城市,当政者不约而同地发动了肃清帐篷的行动。
这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若是失去了自己的标志性景观,而又未能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比如“散步”之类),“占领华尔街”必将很快从公众原本就极难聚集的注意力中消失。不过,对那些持传统左翼立场或怀有那种情结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场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给他们留下了足够重要的启示。
1
经历过漫长的冷战和“历史的终结”之后,天性再乐观的革命家,怕也不敢轻易断言资本主义已经露出行将崩溃的端倪了。“占领华尔街”之最值得注意之处并非它的意图,并非那些屡屡出现在网络视频中、叫嚷“我们反对的是这个体制!”的人的象征意义,而是它采用的方法:抗议者们开发了一种政治表达的新形式,把对苦难的叙述用和平的、幽默的甚至狂欢的方式来装载,每一个人都把“99%”作为他们的Logo。在这面旗帜下,他们持续向不特定的人群开放,接纳新成员,而每一个新成员的加入,都是对一个卷入全球贸易网络的无产阶级化的大众业已形成或正在壮大的有力注脚。与之相对应的,美国是这个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舞台,华尔街则象征了各种不平等现象的策源地。
这个时候, 即便抗议者们只字不提,马克思的幽灵也会在理论家、观察家们的笔下和头脑中接受郑重的招魂礼。
特里· 伊格尔顿( T e r r yEagleton)今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驳难体的新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没想到此书出版不久,伦敦全城(至少在主流媒体眼里)毫无征兆地打砸抢蜂起,然后蔓延到利物浦、利兹、伯明翰、布里斯托等大城市,以至于英超足球联赛都受了株连,托特纳姆热刺队至今还少打一场比赛;紧接着的便是祖柯提公园支起的营帐。伊格尔顿也想不到,这本书会让中国的出版商如获至宝,当作进献给执政党的寿礼。
平心而论, 对读者而言, 单单接受这份急就章式的辩护状所给出的结论意义不大。但是,我们可以借此了解,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对敏感于动荡的全球环境的西方左派学者而言,如何构成一种持续的激励。伊格尔顿坚称,马克思绝不是什么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家,也绝非一意孤行地要给资产阶级一点颜色看看,相反,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推生产力、积累物质财富方面的历史功绩,就反抗而言,他也支持工人参与议会选举,谋求在体制内更大的发言权。
伊氏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种种的阴郁指控,表明他“对历史的极度悲观”,而他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其是在挑动一堆人拔刀拔枪地反对另一堆人,不如说是反映了其对未来的乐观。一如他在历史必然和主观能动之间转圜自圆一样,马克思娴熟的辩证法,始终为社会向着公平方向的改进留住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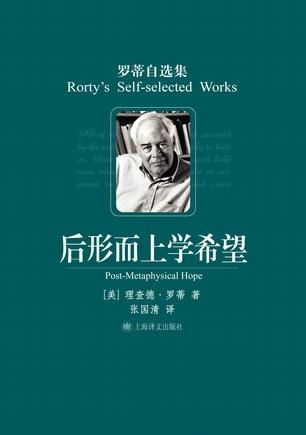
可以断定,眼下发生在美国的事能给伊格尔顿这样的学者带去何种灵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后形而上学希望》里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激发国际左派集体想象力的一股力量彻底消失了,这股力量继承了马克思的一个思维前提(由黑格尔开创),即“模糊了理解世界和知道如何改造世界之间的差异”。罗蒂在这里暗示,或许承认不知道自己怎么改造世界,才保住了改造得以实现的可能;这也是伊格尔顿必然赞同的观点。
与此相应,“占领华尔街”的主要威力——如很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恰恰来自一种“无”性:无中心、无纲领、无意识形态、无具体诉求,只有一些自觉遵行的、保证运动不给媒体落下口实的基本纪律,甚至就连参与者自己,也不知道它将向哪里走去。一位署名阿尤纳·阿达(Arjuna Ardagh)的抗议者写下了这样的评价:“这太棒了,当一个运动并不围绕某个中心来组织,它召唤的就是人们共有的常识心和正义感,而不是对一项教条的效忠。”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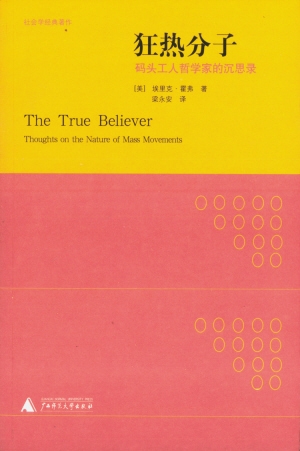
按传统的群众运动理论,明确的指向、美好的蓝图、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加上一种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仇恨情绪,方能激发出参与者内心源源不断的自豪感。在《狂热分子》这本名作中,有“码头工人哲学家”之称的美国人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断言:“一般而言,一个目标具体而有限的群众运动,其积极阶段之持续时间,比一个目标朦胧而不确定的群众运动要短。”他以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为例,认为这两股势力所发起的群众运动“追求的是完全团结和无私的理想社会”,因此才能把“不断革命”的模式给固定下来。
很显然,受制于所处的时代,霍弗的论述集中在那些有若干领袖(或他所谓的“言辞者”)牵头的宏大设计型变革上,他没有考虑到,“目标朦胧而不确定”可以有更多的表现形态——例如,用“占领”而不是“抗议”、“砸烂”、“打倒”来宣说一种否定性的集体情绪。
“Occupy”一词,让人联想到戈达尔等人的电影里,那些停留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观众却不知其为何在那里的路人。抗议运动的参与者们偏偏自豪于自己的不作为,或者做一些与抗议似乎无关的事,如集体做瑜伽之类——这会让霍弗在坟墓里冒出一身冷汗的。
在这个意义上,露营的人们走在了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的前面。当年罗蒂替左派知识分子忧虑,他说,这些人濒临放弃这样的幻想:“与同胞相比,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擅长于在思想中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罗蒂实诚地说,作为一个夹在左右两翼之间的人,他看到了海德格尔所预言的形而上学终结的危机:一个虚无主义荒原的开始,在那里,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幸福将普照人间的价值观,而同时,那些善于从偶然中提纳必然的知识分子将变得无事可做
这番悲观的论调建立在如此的事实上:知识分子缺少一套元叙事话语,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这个资本主义一面筹措资金、组织生产以推动世界运转,一面继续盘剥无产者,把大量第三世界劳动力变成为自己的贪欲服务的奴隶——它已经捂住了知识分子的嘴,我们无法在它早晨九点做业务报表时送上茶和咖啡,而在夜里十二点它关上门喝嫖妓的时候去砸它家的窗玻璃。用罗蒂的话说:我们无法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同时指涉“市场经济”和“所有当代不公正的根源”。
而当运动发生之后,被捂住嘴的成了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索罗斯的口头支持(或者说卖乖)并不太出人意料。他说,最令抗议民众愤怒的还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救银行,而是已经陷入困顿的银行还让执行主管领取高额红利奖金——这是看得见的不公,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赞同他们的看法”。相反,左派学者里向来极具人望的齐泽克跑去演说,大谈“这个世界肯定是有问题的”,却露出一根机会主义的尾巴来——如果这个运动当真需要什么思想和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演说家和煽动家,恐怕早就八抬大轿,去搬他老人家出山了。
不作为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无诉求。“你们要什么?我们做个交易吧!”这种用来安抚罢工的惯有的恩赐态度,抗议者根本不给华尔街的富豪们以表演的机会。没有诉求,此刻要比“把旧制度打个落花流水”听起来更加有力。而他们的坚持,也让上来就投以冷眼的观察家们(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抗议要有抗议的样子,比如,你要列出想让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奥巴马新政被右翼势力肢解,或者举出新政中需要修改的内容,或者告诉执政者,人民希望他们在就业、医保、银行监管方面做些什么)不得不一个个调整最初的看法。
这是一次革命还是普通的暴乱呢?凡尔赛宫中的路易十六困惑到。阿达在他的博文里说:我们希望它变成一场不一样的革命。
3
保守派一边的人,大量的共和党人包括总统候选人,都把“占领华尔街”鄙夷为与“茶党”相对应的激进左翼活动,一个“插曲”。不过,很多观察者所指出的令人嗟呀的多元性,是这个所谓的“插曲”的价值的体现:尽管整个运动没有明确的诉求,但参与者的怨气来自各个方面,有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过重,有的是受歧视的少数族裔,有仅仅是家里境况不好,自己又“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举着牌子往“99%”的队伍里一站。有警察穿着制服加入了抗议者的人群;有海军士兵安营扎寨;有犹太人,也有穆斯林;公交车司机和消防员都戴着让人一望便知的工作帽。
这种多元性里当然包含为数不少的挟私分子。例如在民间不怎么受欢迎的工会,就趁机到现场去招募新成员,物色伶牙俐齿的发言人;流浪艺人并没有兴趣与抗议者们长期同在, 只是习惯性地凑个热闹而已;一些人数极少的民间教派也看到了机会。《纽约时报》刊发了马克· 奥本海默( M a r k Oppenheimer)的文章,他观察到,有宗教信仰的抗议者们在各自的营帐里举行敬拜仪式(例如犹太教徒的赎罪日斋戒),基督教抗议者还组成了布道小团体。但是,小团体之间并不像当年法国“五月风暴”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一样,个个都号称自己掌握了革命的钥匙,相反,在长居户外、共同露营的环境下, 他们友好地交换彼此的信仰、饮食和日用品。假如这种奇特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如奥本海默所说,已经在远至多伦多的抗议者群体之中发生,那么,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再像个乡愿似的去怀念街垒和大字报。
《纽约时报》毕竟是立场偏左的。就算没有政府的武力弹压,抗议运动的兼收并蓄,事实上也埋下了它从内部瓦解的危险,而且,这种可能性只会随时日迁延、阵容壮大而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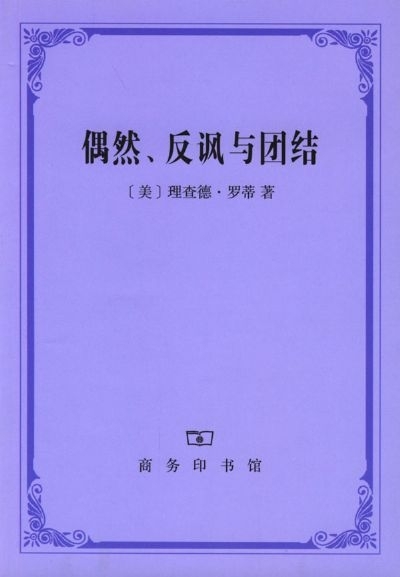
理查德· 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从一个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俄国革命式集体运动彻底绝望后的反省。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不要企图让所有人都停止私人的规划,一同去抵御公共的危险;一个人(这话又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所笃信并潜心追求的、比他自身更伟大的东西,例如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不必然地与他对别人所承担的道德行为相干。
拿到眼下的事实中来说,就是你把你的帐篷匀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随便哪个外来客,并不意味着你就和他对同一个剥夺了你们的居住权的资产阶级敌人有了共同的、坚不可摧的立场和态度。
像一个被炮弹轰掉一条腿的角斗士一样罗蒂有些恶狠狠地把那些知识分子的冷兵器——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扔在了脚下,而代之以从尼采等人那里得来的历史偶然性。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暂时的团结,这种为赤诚的自由主义者所倾心的景象,纯系出自偶发,而一旦将其形而上学化,仿佛有贯注其下的人性本质做依托,将来就要遭受两难或多难的困境。
这种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你同时隶属于一个宗教团体(尽管也是抗议性的),又隶属于一个大的政治抗议团体的时候,你势必会负有两种以上的义务,大团体的道德义务和小团体私人承诺之间,难免会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和我是因为什么而团结,你和我又可以团结多久?
罗蒂只满足于做半个尼采——他悲观于现世,却并未因此狂歌五柳前;与他形成对照的,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的《希望的空间》是一本格调奋勇的书。在书中,他指出了一个强悍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工厂消失或不稳定、永久性工人组织变得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如何既不走回列宁主义的传统左翼先锋老路,也不求诸左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先锋,来组织政治集团进行斗争。
哈维描述了在他的家乡巴尔的摩,一个由教会发起的、扩及全城范围的为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如何持续存在:它不以传统的劳动组织模式来操作,而是非常先进地以适应新环境的方式运行。哈维说,这个运动融合了种族、性别、阶级所关注的问题,其成功的经验之一,正是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之间实现了同盟。哈维把自己的研究定性为探索“乌托邦机遇”,这当然不是什么关于人间天国的迷梦,而是事关新的组织形式的形成。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可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现,问题就在于如何去组织,去综合其力量。
哈维的书中没有关于“团结”的考量,这个词未免过于书生气了。但是,这不妨碍把团结与否看作估量一个群众运动的生命力的最直观的标准。
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形成的同盟毕竟还走不出巴尔的摩,而“占领华尔街”却撒豆成兵一般地扩散其规模。聪明的组织者们似乎知道应该怎样把零散的手指攥成拳头。看到专为捱冬所准备的16×16英尺的帐篷和11×11英尺的帐篷搬进祖柯提公园的景象,你会感到,这些抗议者们好像已准备好了要接受气温和凝聚力的双重试炼。
4
左翼没有乐观的理由,资本主义早晚要用无产阶级的营帐装点自己的风景。对不知去向何方的抗议者们而言,营帐存在一天,试炼便将进行一日。要推进一场政治运动,在自己的阵营里“求同存异”殊非易事,必须指靠每日迫在眉睫的行动;而谁也不敢说,一对水火不容的私敌能在营火晚会里前嫌尽弃,干戈玉帛——若真能如此,马克思预言的理想社会也不至于一再延期,成为一种无法证伪的政治弥赛亚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理查德·罗蒂否弃了康德对“我们可以指望共同人性”的预设:“如果我们把道德进步的希望托付给了同情心,那么我们实际上把它们托付给了恩赐。”
尽管如此,罗蒂依然承认《共产党宣言》的魅力:__“对于社会正义的希望仍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人类生活的唯一基础”,他也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富人和穷人的关系问题。”这便是那些一屁股坐下来安营扎寨的人,在这个秋天小心翼翼地测探的社会共识——最坏的测试结果,也不过就是卷铺盖回家各找各妈。
然而,形势的进展很可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这个芝加哥的贫民区与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看起来不分彼此的同一化时代,不满的不仅仅是那些自封的“99%”,同样,在这个任何底层反抗都可能砸掉其他无产者饭碗的全球化大生产时代,祖柯提的人们得到了免费的食物、日用品、书籍、医疗和法律服务。大多数美国民众对这一抗议并无半点关心,积极响应的只是少数人,但是,这种待遇,毕竟是罗马和伦敦那些被公共舆论一面倒地痛斥为“不知羞耻”、“践踏法律”的暴徒无法想象的,也是曾几何时,从别人手上夺下索尼相机、砸坏路边的丰田汽车的中国反日分子们无法想象的。
它的“无欲则刚”是策略,也是一种诗学。诗学的功效是点燃人们的想象力。因为“无欲”,所以它也没有边界;因为“无欲”,所以它并不像上世纪名声已坏的试验者们那样,对着“不断革命”、官僚建制、利益集团等一碗碗苦汤狐疑不决。
我还记得,十二年前的那个五月,许多人只是“占领”了美领馆外的空地,但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命名为“抗议”和“打倒”。也许是知道第二天就要各奔前程,所以心心念念毕其功于一役吧。在这场旌麾猎猎的“咸与”中,偶尔也会响起因互相推搡引来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羞愤叱喝,让我想起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写到的,那些顶着马克思、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的头衔、互相以邻为壑的左派营垒。
罗蒂是对的:不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核心自我”,可以把人,这群嘤嘤嗡嗡的政治动物牢固地、长久地攥到一起。知识分子压根就不应该往那个方向去想。
相信自己有义务使未来比现在更可取的知识分子们,可以持守的只是想象力。在“列宁主义的终结、哈韦尔和社会希望”一文中,罗蒂写到了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那个时候,就连哈韦尔本人,都不知道那场革命
将如何进行下去,他带着个戏剧家的头脑,“似乎准备全力以赴地致力于用没有根据的希望取代理论洞见。”他像一个半醉的夜归者,一个颓废的人,这种颓废来自于他唯一确知的东西,那就是他自己的局限,就是个体的主张,只是恒河沙数的细小琐屑之一,只有被拼凑、被汇聚、被滚雪球的可能。然而,就在拼拼凑凑、错进错出之中,布拉格的人们放弃了杜布切克,用充满了偶然与反讽的个体抉择,将国家拨到了一条现在看起来最优的轨道上。
当工人阶级果真按马克思的理论揭竿而起、反对培养他们的体制时,他们会不会乐意接受一个被历史安排好的“掘墓人”角色?自由与必然的辩证让理论家感奋,却未尝不会让实践者踌躇。如果俄狄浦斯预先知道自己要去弑父,他会去埋怨拉伊俄斯,还是去埋怨为他刻下了悲剧结局的索福克勒斯呢?
我想过这个问题。所以, 我认为现在就尝试在左派运动的地形图上绘出“占领华尔街”的位置必将大错特错。一种取代了政治神学的希望诗学(不管它是不是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不允许知识分子再犯这样的愚蠢。毋宁说,当年罗莎·卢森堡在狱中引以自我激励的那句新教改革家乌尔里希·冯·胡顿的话“我挑战过了!”,更接一个坚定的反资产阶级人士应有的精神状态。
这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在《新共和》的评论员沃尔特· 夏皮罗(Walter Shapiro)眼里只有给媒体充实谈资的价值的路。他挖苦说,在“常规戏码”迟迟未开锣之前,“占领华尔街”还只能是一场闹剧:“我也认为,严肃的记者们一直在等待一些人跳出来愤怒地咆哮,控诉华尔街的寡头们成天拿着年金开怀大笑的样子。”他没有看到那非常规的戏码早已开场,或者,只是不愿承认。